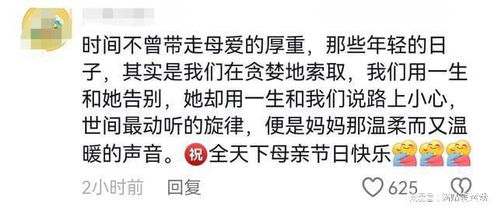2025年3月,长和(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全球港口资产,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出售给美国贝莱德财团,这一交易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在特朗普政府多次对巴拿马运河问题施压的背景下,长和为何仍然如期推进这一交易?本文将深入探讨长和决策背后的多重考量,以及这一交易对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的影响。
长和决策的商业逻辑
长和此次出售的巴拿马港口资产,不仅是其全球港口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黄金水道”巴拿马运河的核心枢纽,自1997年起,长和便取得了这两个港口的经营权,并一直运营至今,近年来,这些港口资产面临着多重挑战。
巴拿马政府迫于美国压力,自2024年底开始审查和记港口的运营合约,甚至威胁终止合作,这一政治风险使得长和的运营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巴拿马运河近年因干旱、地缘冲突等因素导致吞吐量缩水,运营成本激增,数据显示,尽管这两个港口年净利润达13亿美元,但其运营风险正不断攀升。
在此背景下,长和选择将港口资产出售给贝莱德财团,无疑是一次明智的商业决策,贝莱德财团以13倍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估值溢价收购,远超行业平均10倍的水平,为长和带来超过190亿美元的现金回流,这笔资金将极大缓解长和融资成本上升的财务压力,改善其财务状况,交易完成后,长和的净负债率将从23.6%降至18%以下,使得公司的财务结构更加稳健,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长和股价在消息公布后的暴涨也充分反映了市场对这一交易的积极评价,投资者对长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为此次交易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
地缘政治的博弈与影响
长和巴拿马港口交易的背后,交织着地缘政治的博弈,巴拿马运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海运通道之一,承担着全球约6%的海运贸易量,每年有超过9900艘船舶通过,它连接着太平洋和大西洋,是国际贸易的关键枢纽,中美日三国占据了其74.7%的货运量,使得巴拿马运河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对巴拿马运河问题施压,宣称要“收回运河控制权”,甚至不惜以制裁相威胁,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给长和旗下的港口资产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长和选择在政治压力达到临界点之前“高位套现”,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避险策略。
通过出售港口资产,长和不仅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资产损失,还能在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及时抽身,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决策也被部分舆论批评为“向美国霸权妥协”,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曾多次威胁“武力夺回运河控制权”,长和的迅速脱手被视作对美方施压的回应。
中美战略竞争的缩影
长和巴拿马港口交易不仅是商业巨头的高位套现,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缩影,巴拿马运河的战略价值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美国通过贝莱德财团间接掌控运河港口,实质上是重构全球供应链控制权的重要一步。
数据显示,美国40%的集装箱运输依赖巴拿马运河,而中国作为运河第二大用户,每年有超1000艘次货船通行,承担着中拉贸易30%的货运量,美国若通过港口运营权提高中国船舶通行费、限制靠泊优先级,甚至以“国家安全”为由扣留中国货轮,将直接冲击中国外贸命脉。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表态“尊重巴拿马主权”,但已加速布局替代通道,如秘鲁钱凯港建设、尼加拉瓜运河计划以及中欧班列扩容等,旨在降低对巴拿马运河的依赖,短期内美国对运河咽喉的掌控仍可能削弱“一带一路”在拉美的推进效率,凸显中国在海外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被动局面。
长和的未来布局与挑战
长和此次出售巴拿马港口资产,是其全球化计划的一部分,长和一直在甩掉那些沉重的资产,转身投向医疗和科技这些能飞速增长的领域,这一交易将为长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使其面临新的挑战。
长和需要在新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弥补港口资产出售带来的收入缺口,长和还需要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业务的影响,在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长和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和管理风险,以确保其业务的稳健发展。
对中国的启示与应对
长和巴拿马港口交易对中国而言,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这一交易暴露了全球化退潮时代企业的两难:跨国公司需在政治风险与商业利益间平衡;国家战略与资本逐利的矛盾日益尖锐。

对中国而言,这一案例提供了三重启示:一是强化海外关键节点的自主可控,加快布局替代性港口与陆路通道,推动“一带一路”多元化;二是完善企业海外投资保护机制,通过多边协议、保险工具等抵御政治风险;三是推动国际规则重构,联合新兴经济体倡导航运中立原则,抵制单边霸权对自由贸易的侵蚀。
中国还需要加强海军力量建设,提高海外护航能力,以确保中国货轮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通行,中国还应积极参与国际航运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航运秩序。
长和如期推进巴拿马港口交易,是商业决策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的复杂结果,这一交易不仅折射出长和家族在动荡国际局势中的生存智慧,更揭示了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深层挑战,对中国而言,唯有在坚守开放的同时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网络,方能在变局中掌握主动权。